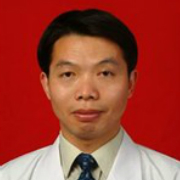-
- 麦志广副主任医师
-
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科室:
中医科
- 宗萨钦哲仁波切开示的“金刚经”...
- 我的微博地址
- 关于在广医四院开诊
- 关于预约和就诊
- 该不该吃肉(第十七世大宝法王重...
- 关于增加开诊时间
- 叛逆的佛陀(作者:本乐仁波切)
- 看到的就是真的吗?
- 真正的出离心其乐无穷(宗萨钦哲...
- “出离”的真意(宗萨蒋扬钦哲仁...
- 俞敏洪:我让女儿主动学习的秘密...
- 两位智者关于冥想的探讨
- 春之祭
- “房产税”?
- 九点九秒的启示
- 我问佛(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 少吃少穿的好处
- 一寸河山一寸血(有心人请看同名...
- 高通胀下的便宜货
- 十诫(仓央嘉错原创,非诚勿扰)
- 信以为真(非诚勿扰)
- 声讨珠心算的教学
- 大人先生传(阮籍)
- 明就仁波切十一月香港行程
- 为什么我爱哈里法克斯(宗萨钦哲...
- “怀念顶果钦哲仁波切”纪念文(...
- 《山楂树之恋》小感
- 见与不见(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
- 怀念我们共同的导师
- 世博经历(杨恒均)
- 有很多方式可以浪费人生
- 教你打坐1:科学是什么玩意
- 关于艺术
- 周有光: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 摄受具器弟子(密勒日巴尊者作,...
- 大恩上师仁波切父亲节贺词
- 自身与环保
- 转恶缘为道发愿文(堪布贡噶旺秋...
- 我的堪布??贡噶旺秋
- 职业性格测试
- 大恩上师仁波切母亲节贺词
- 诊室空气不流通,请各位支招
- 当医生也举起屠刀
- 找不到我看病怎么办?
- 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信
- 想起我的英雄
- 吃饭的方法
-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寅恪)
- 王观堂先生挽词(陈寅恪)
- 毛泽东与医生畅谈生死(自人民网...
- 道家医学的精髓:从养生长寿到“...
- 灌顶(邱阳创巴仁波切)
- 纪念许老师
-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 让孩子的人生起点高一些(孔庆东...
-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李一道长)
- 医有神医,有人医(刘一明)
- 禅修心法??正确的修行态度
- 缙云山7日闭关之得(我身旁重庆...
- 我最想要的是......
- 无从选择??关于爱心工程的一席...
- 强梁者,不得其死
-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
-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
-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
-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
- 十干体象
- 谁首先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美国...
- 宗萨钦哲仁波切2004年开示的...
- 噶玛巴千诺
- 冷水擦身或冷水浴的操作
- 非洲出现新致命病毒
- 不能上传音乐,只好从哥德巴赫说...
- 08年的最大损失
- 考试之后
- 倒霉的夏枯草
- 疯狂的病毒,疯狂的猪
- 少则得,多则惑
- 谷神不死
- 从《内经》想到今年气候
- 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村上春...
- 关于咳嗽的忌口
- 宗萨钦哲仁波切开示的“金刚经”...
- 濒湖脉学之沉脉(李时珍)
- 2009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 濒湖脉学之浮脉(李时珍)
- 医道合一(摘自伤寒论坛 作者:...
- 如何学习《内经》(任应秋)
- 医疗行业算是服务行业吗?
-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陈寅恪)
- 论人类误判心理(查理?芒格)
- 简单的人生(芒格)
- 查理?芒格的妙语
- 好好发心
- 学习科学发展观心得
- 从《黄帝内经》对人体时间节律的...
- 比坏银行更好的办法
- 熟视无睹的障碍
- 一点两面战术
- 研易之一??水地比
- 体检中心几种典型的商业模式
- 恩师索达吉堪布关于儿童参加读经...
- 菩提心的两个阶段之实修
- 深切的虔敬心:面对情绪感受
- 降息对穷人的影响
- 价值投资的智慧
- 直言无忌丘成桐
- 大富翁游戏的误导
- 穷医生的理财入门
- 又降息了
- 去年秋天宗萨钦哲仁波切对大陆弟...
- 水多木漂之案
- 重阴必阳
- 师徒问对
- 《心经》??宗萨钦哲仁波切(2...
- 没有所谓的“真实故事”
- 这不是神通
- 面对高通胀
- 业余医生懂看病吗?
- 今天不能让我死啊
- 是什么让一位中国母亲变成了“贼...
- 你吓过病人、骗过病人吗?
- 怎样让病人觉得你爱他?
- 中医的存与废
- 机率如何左右你我的命运和机会(Leonard Mlodinow)
- 作者:麦志广|发布时间:2009-11-13|浏览量:1078次
记得我年少时,常在安息日望着烛台上跳跃的烛火。当时我的年纪还感受不到烛光的浪漫,只觉得烛光在墙上映出忽明忽暗的影子,十分神奇。影子一下子移动,一下子变形,或长或消,看起来不像有什么道理或规则。那时的我,相信烛火的摇曳有其韵律与理由,有一定的模式,是科学家所能预测的,还能用数学方程式来解释。
“人生并非如此”,父亲告诉我,“世事多半是难料的。”他说当年他被囚禁在布亨华特(Buchenwald)集中营时,有一次因为饥饿,偷了面包房的一条面包。面包师傅要盖世太保把有嫌疑的人全都集中起来,然后问:“是谁偷了面包?”没有人承认,结果他们打算将嫌疑犯一个个地枪杀,直到全部杀光或有人承认为止。父亲挺身而出,救了大家。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麦志广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想当英雄,只是想到横竖都是一死。谁知道面包房师傅并没有杀他,反而给了他一份助手的工作。“这就是机运”,他说,“这事本与你无关,但是换个结果,就不会有你了。”
我发现自己能够活在世上,居然要感谢希特勒,还真叫我大吃一惊。德国人杀死了父亲的前妻和两个孩子,抹掉了他的前半生。如果不是战争,父亲不会移民到纽约,不会碰到我的母亲,也不会有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了。
父亲很少谈到二次大战,我当时并不明白,几年后才恍然大悟。他谈到自己的痛苦经历时,并不是要我知道他的经历,而是与我分享生命中更大的教训。战争是个极端,但是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基于极端。生命的轮廓就像烛火,随着各式各样的随机事件不断地向新的方向伸展,再加上每个人作出的反应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也不同,因此生命难以预料,也难以诠释。
就像看着罗氏墨渍测验(Rorschach blot)时,可能你看到的是麦当娜,而我看到的是鸭嘴兽,我们所接触的资讯,不管是商业、法律、医药、体育、媒体,或是你儿子的成绩单,都有许多方式可以解读。然而,不同于解读罗氏墨渍,诠释机遇所扮演的角色,有正确方式与错误方式之分。
人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往往会凭直觉来衡量与抉择。面对一只对着我们呲牙咧嘴而笑的老虎,是因为吃饱了而快乐,还是因为饿昏了而把我们当成饱餐的对象?在这种生死一线间,能凭直觉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无疑具有演化上的优势。不过,当今世界的损益计算方式不同于草莽时代,光凭直觉的决断过程有其缺点。
面对今日的老虎,这种惯常思维方式下的决策,往往并非最好,甚至还十分不妥。对研究脑部如何处理不确定状况的专家来说,这些结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许多研究指出,脑部负责评估意外情境的部分与掌管情绪(也就是不理性的主要根源)的部分有紧密的联系。
例如,功能性MRI(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多巴胺系统掌控着对风险及报偿的评估,而这种系统是脑部的一种报偿回路,对激励及情绪过程十分重要。MRI影像也显示,与情绪状态(特别是恐惧)有关联的杏仁体,也会在我们基于不确定性而作出决策时活跃起来。
人类用来分析偶发情况的机制,是综合了演化因素、脑部构造、个人经验、知识与情绪等的复杂产物。事实上,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复杂,有时候脑内不同部位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彼此竞争以取得主导。
比方说,每当你吃了虾,四次中有三次,你的脸肿大了5倍,负责“逻辑”的左半脑会设法找出一个模式,而负责“直觉”的右半脑则干脆说:“别吃虾了。”至少,这是研究人员在没那么痛苦的实验安排中发现的??这个游戏称为“几率猜测”。代替虾及过敏反应的,是一连串两种颜色的卡片或灯光,比方说绿色和红色,每种颜色出现的几率不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模式可循。例如,红色出现的几率是绿色的2倍,就像“红-红-绿-红-绿-红-红-绿-绿-红-红-红”等等。受试者要做的,就是在观察一阵子后,预测下一个出现的是红色还是绿色。
玩这个游戏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每次都猜出现频率较高的颜色,这是老鼠和其他动物偏好的策略。采取这个策略,可以保证一定的猜中率,但也得认命结果可能不会更好。比方说,绿色出现的几率是75%,如果每次都猜绿色,猜中率就是75%。
另外一种策略,就是让你猜红猜绿的比例“吻合”先前观察到的红绿出现的比例。如果红绿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而你又看出了这个规律,这个策略就能让你每次都猜对。不过,如果红绿的出现是随机的,第一种策略的结果较好。当绿色随机出现的几率是75%时,采用第二种策略,在10次中大约只能猜中6次。
人类通常都想找出规律,而在这方面,我们就被老鼠比了下去。
有些人的脑部遭受过某种手术创伤后,左半脑与右半脑的沟通被截断(称为裂脑),如果对这些病人进行几率猜测的实验,只让他们用左眼看卡片或灯光,并以左手表达他们的猜测,这样就成了对他们的右半脑进行实验。如果实验只牵涉到右眼及右手,就是对左半脑的实验。研究人员对这些病人进行了一连串的实验,发现右半脑总是猜较常出现的颜色,而左半脑总是想猜规律。
面对不确定性而能作出明智的评估,是一项难得的技能。可是就像所有的技能一样,靠着经验就能改善。下面我要审视机遇在周遭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角色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种种因素。
英国哲学家及数学家罗素曾说:“我们都是以‘素朴实在论’为起点,也就是认为万物正是它们所显现的样子。我们认为草是绿的,石头是硬的,雪是冷的。可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草的绿、石头的硬、雪的冷,并不是我们从自身经验得知的草的绿、石头的硬、雪的冷,而是相当不同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随机性”的镜头探视生命,我们会发现,生命中有许多事物并不全然就是表面上所显现出的样子,而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奖赏有效,惩罚无用?
2002年,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今天的经济学家涉足各式各样的领域:他们解释教师的薪水为什么那么低,美式足球队为什么那么值钱,猪的生理机能为什么限制了养猪场的规模(猪的排泄量是人类的3到5倍,拥有几千头猪的养猪场制造出的排泄物,远超过邻近的城镇)。
纵使经济学家作出了很棒的研究,令人不解的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却不是经济学家。卡尼曼是心理学家,数十年来与特弗斯基(Amos Tversky,1996年去世)合作,一起研究并澄清了大家对“随机性”的种种错误诠释,这些误解正是本文即将谈及的许多谬误的源头。
在了解“随机性”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虽然随机性的基本原则来自日常的逻辑,但由这些原则导致的许多结果却违背直觉。卡尼曼与特弗斯基的研究就是因一桩随机事件的激发而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尼曼还是希伯莱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他答应接下一份不怎么有趣的工作:向一批以色列空军飞行教官讲解行为改变的一般观念及其在飞行训练心理学中的应用。卡尼曼清楚地解释了奖赏有效、惩罚无用的观念。有名学员打断了他,提出反驳,就此使他顿悟,引导了他往后几十年的探索之路。
“我通常会称赞学生完成的巧妙飞行动作,结果他们下一次总是会退步”,打断卡尼曼的飞行教官说,“对学生的不佳表现,我会大吼大叫,通常他们下一次都会进步。你怎么能说奖赏有效、惩罚无用?我的经验并非如此。”其他飞行教官也有同感。
卡尼曼认为,飞行教官的经验似乎是对的。但是,卡尼曼也相信那些证明了奖赏有效、惩罚无用的动物实验。反复思索这个显然的矛盾之后,卡尼曼突然意识到:吼叫斥责只是发生在进步之前,但与表象相反的是,它并非进步之因。
这怎么可能呢?答案就在“回归到平均值”(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这个现象中。意思是说,在纯碰运气的情形下,在一连串随机事件中,紧接着不寻常事件之后发生的极可能是一个普通事件。
情况是这样的。
战斗机飞行学员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能力,要提升他们的飞行技能牵涉到很多因素,也需要大量的练习。当技能经由练习逐步提升时,进步的程度在连续两次的飞行中很难看出来。一次特别好或特别差的飞行,多半就只是运气罢了。也就是说,如果某位学员做了一次特别漂亮的降落,远远超出他的正常水准,那么,回到正常水准的机会就很大,也就是下一次的表现会差一些。如果前一次教官称赞了他,自然就显得“称赞无用”。
但是如果该学员那天做了一次特别糟糕的降落,例如冲出了跑道,冲向空军营地餐厅里装海鲜浓汤的大汤桶,那么,第二天回归到他的正常水准的几率就很高,也就是表现进步了。如果他的教官习惯于在学员表现差劲时大吼“你是猪头啊!”,看起来就像“斥责有用”。
于是,一种“表面的”模式就出现了:称赞学员表现佳,会有反效果;学员表现差劲,教官大吼,把他比作畜牲,然后学员会进步。卡尼曼班上的教官就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到大吼是有效的教育工具。其实,这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差别。
这种直觉上的错误,刺激了卡尼曼去思考:这样的错误想法是普遍现象吗?我们是否也像那些飞行教官一样,相信粗暴的责骂可以改善孩子的行为、员工的表现?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时,是否还有其他错误的想法?
卡尼曼知道,人在作判断时,必然会运用某些策略,来简化这个判断的复杂程度,而与几率有关的直觉,在简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吃了街边小摊贩令人垂涎三尺的炸玉米饼之后,你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碰到这个问题,你不会真的去回想那些你曾经光顾过的路边摊,然后算算事后吞下的胃药,得出一个估计数字,只凭直觉回答就是了。
然而,20世纪50及60年代早期的研究却显示,人在面对“随机性”时作出的直觉反应,在这类情况下失灵了。卡尼曼想知道,这种对不确定性的误解到底有多普遍?这种误解对我们的决策过程又有什么影响?
几年后,卡尼曼邀请一位年轻教授特弗斯基进行客座演讲。午餐休息时,卡尼曼向特弗斯基提到正在自己脑中成形的想法。接下来的30年里,卡尼曼和特弗斯基发现,就连在复杂的题材上,不管是军事或运动赛事、企业困境还是医学问题,只要一牵涉到随机过程,人的信念与直觉就会经常“出轨”。
TA的其他文章: